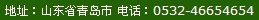|
文/丰建国 图/刘志军 在丰镇这座老城里,上点岁数的人都记得有些年,随处都可见人们剥云母。这活儿大部分是女人们在做,男人剥云母的很少。一来是男人生性爱动,耐不住长久坐在那里不挪“窝”;二来男人手指粗且僵,不易剥云母。剥云母这活儿要的是手上功夫,是一种轻巧的营生。 云母是一种矿石,这种矿石有别于其它矿石,就是一层一层易剥离,不像别的矿石是浑然天成,要想让它有所改变或成为一种人们需要的成品,是需精准的专为“它”而制作的工具。 云母的剥离,需一把轻巧的云母刀。这种刀是用小钢锯条改制而成。把钢锯条的一端削成一个又尖又圆的刀锋,再把它磨得光光滑滑的。有的人在小钢锯条的另一端挖一个小孔,系一根红毛绳或彩绸,这样剥云母时便只见一点红在闪,一团彩在舞。我想这种点缀,便是给单调枯燥的工作,带来那么一种情调和活泼吧。 那时县城有云母厂,在那里上班的女工很是“牛”气。她们穿着类似医生的白大褂,戴无沿白帽、白口罩。还有许多学校,也开办了云母车间。其实除了这些专门的工厂车间和女工聚合在一起剥云母外,县城里许多闲散的和待业的女人都剥云母。她们在自己的家里剥,也在户外剥。在我的印象里,当年县城的最大亮点和看点莫过于剥云母了。那几年因我父亲是右派,我们已被遣迁到乡下。每年的寒暑假,我便会回到县城,在姐姐家,帮着照看几个年幼的外甥。那时我的姐姐就是一个云母工,她每天按着钟点到一中上班。 看姐姐剥云母,是种享受。她左手拇指和食指夹一片云母,右手把云母刀的尖插进云母层,一掀一掰,一块的几层云母被剥离开来,然后就只听飒飒如风声,脆脆如冰裂的声响;薄薄的云母按大小尺寸被剥成薄厚等同的云母片。成品的片放在面前大小不等的硬纸盒里。盒子大都是医药盒,诸如葡萄糖、青霉素等药盒,姐姐用一双灵巧的手,把一块块云母石片剥离的烁烁银星飞散,片片晶亮如冰。姐姐的表情如平静的湖面,长长的睫头,挺拔的鼻和红润的唇,像旧画里的美人儿。每每想起那场景总有一种清苦中的快乐。 西巨墙街、东巨墙街、西南园巷、顺城街、毛店街、八大股……老县城的巷口院门,时时会看到剥云母的人,有的二三人,有的四五人。她们说着县城新闻和邻里旧事,嘴不住手不停,每人跟前摊三四个硬纸盒,女人们又看门又做活。那年头,共同的贫困让人们没有攀比的陋习。剥云母,折射着老县城社会的一幕。阴天无风在户外,冬有阳夏有荫,聚在一起剥云母,彼此的心灵便会有了感应,清苦的生活就有了盼头。 云母虽是矿石,它被小刀一层又一层剥离;至于它的用途,有人说制造飞机用,有人说制造高晶管。真的运往哪儿?剥云母的人谁也不知道,她们只知道剥云母按斤论两能挣钱。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人们生存在禁锢的“圈里”,活着就得想辙;有了辙,社会、家庭才会持续、发展。 赞赏 长按吡美莫司乳膏治白癜风效果如何全国治疗白癜风最好专科医院
|
时间:2017/8/6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丰镇人童年的记忆
- 下一篇文章: 丰镇要在北山附近建古街了速来围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