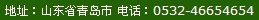|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见母亲默默地流眼泪,也不知为什么。小孩子无从洞察大人的心理,也根本不懂洞察,我只是用稚嫩的小手,为母亲拭去眼角的泪花。当我长大后,经历了两次刻骨铭心的事件,才懂得母亲为什么经常流眼泪的原因。 父母婚后,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儿,在刚满月时就夭折了。那时父母也年轻,虽然丧女,但也没有造成太大的伤痛。后来相继生了我和两个弟弟,两个弟弟又都相继夭折了,大弟弟夭折时八个月龄,小弟夭折时已过一周。这样就对父母造成很大的伤害,尤其是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哪一个孩子不是母亲的心头肉,连续的失子之痛,怎能不令她痛心万分。那时我只有四五岁,根本不懂世事,只是拉着母亲的手说:“妈,我想和弟弟耍”。每当此时,母亲总是把我搂在怀里,默默地流泪。 后来又生了我妹妹,这给受伤的父母带来快慰。妹妹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很快长到了五六岁。父母对我和妹妹疼爱有加,那时生活虽然清贫,稍微有点好吃的,都紧着我俩吃,吃在我们的嘴里,甜在他们的心头。 当我十二岁那年,我的二妹妹出生了,这给家里带来了新的生气,也增添了不少欢声笑语。连我和妹妹对小妹都喜欢的不行。虽然母亲没有奶水,好在生产队的母牛相继下犊,父亲经生产队同意,挤点牛奶喂小妹。直到第二年,小妹已过完生日,已经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了。灾难再一次降临我们这个不幸的家庭,父母结痂的心灵伤疤再一次被揭开。 春季本就是个疾病多发的季节,小妹毕竟还小,抗病力差,她有病了,咳嗽不止,还发高烧。这下急坏了父母,到处找医生给小妹治病。医生走马灯似的来了走,走了来,但就是不见效,而且还不断恶化,到后来连饭也不吃了。看得出,父母的心头已罩上了阴云,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他们没有放弃,又从公社卫生院找来一个大夫,一量体温不足三十五度,问父母喂了什么药,说是上个大夫给配的四环素。大夫摇了摇头:“你们的孩子恐怕是救不了了”。说着就准备要走,这下母亲急了,放声大哭,拉着大夫的手:“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她没了我怎活呀!我已经撂了三个孩子了,不能再没有她了”!大夫看我母亲哭得可怜,再次摇摇头,唉了一声:“试试吧,我给打一针”!说完就给小妹打了最后一针。打完针大夫马上就走了。大夫走后,我将装药水的小玻璃瓶拿起来,看见上面写着注射用水。那时也不知道注射用水是什么药,只希望这一针能把小妹的病治好。可事与愿违,不到中午小妹就没了。 这次母亲反而没哭,只是将小妹抱在怀里不停地说:“润桃好好睡吧!妈妈在这儿,你别怕,妈妈在这儿,你别怕,别怕”!一个劲地唠叨,父亲毕竟是男子汉,还算理智。小孩死了不能像老人去世那样,花棺彩烟的安葬,死了就不能再放在家里了。父亲又去找三娃伯伯了,三娃伯伯已不是第一次给我们家扔死孩子了。不多时三娃伯伯就来了,准备好莜麦秸,进家后就对我母亲说:“德仔家,你这娃娃怎抱的,来三娃冈(哥)给你抱抱”。边说边顺势就从母亲怀里将小妹抢过去,从门外就走。母亲这时似乎也反应过来了,就往外追三娃伯伯:“还我孩子,还我孩子”,别喊边哭:“大三娃你个天杀的,妈呀!你还我孩子……”三娃伯伯头也没回,用莜麦秸将小妹一裹,解下腰间的麻绳一捆,夹起来就朝村外走。母亲和父亲仍在不停地撕扯,想要挣脱父亲。母亲经过一阵和父亲的撕扯也累了,三娃伯伯也走远了,索性坐在地上边哭边不停地撕扯自己的头发。到后来连哭声也没有了,只是嗷一声嗷一声的吼。 早晨的天气还清空万里,转眼间天空变的灰朦朦的,太阳只有一个淡淡的影子。门前的那棵大榆树上的乌鸦叫个不停,让人心烦意乱,使我们正在经历伤痛的家庭,好像又罩上了一层阴影,但似乎又是在诉说着我们家的不幸。这天母亲没有给我们生火做饭,家里倍觉冷清,没有了往日的活泼气氛与温馨。母亲坐在炕头上一会儿发呆,一会儿拿起小妹的枕头闻闻。父亲在地上走来走去。 这天我成了家里的主人,喂猪、喂羊、做饭,别的饭我也不会做,晚上我熬了一锅和子饭煮山药,妹妹和我吃了,父母连碗也没端,劝他们也不理。收拾完晚饭,我早早地将被子拉开焐上。母亲仍然坐在炕头上,父亲靠在母亲的旁边,妹妹爬在母亲的腿上打盹。锅台上的煤油灯结了一个大大的灯花,遮住了半边光亮,一闪一闪显得特别昏暗,映在母亲的脸上,显得特别苍白。 正在我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从窗外传来幽幽怨怨“呜——”的一声,听起来很像是小妹的哭声,母亲最先做出反应:“润秀起来,润桃回来了,妈给开门去。”说着就将妹妹推开,就要下地。我们谁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只听的嗵一声,母亲一头栽到地下。我急忙跳下地一看,母亲的头磕在顶风箱的磨石上,血已经流了一脸,我上去拉母亲,她却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这下我吓坏了,我别哭别喊:“大大,大大”!抬头再看父亲,仍然靠在墙上,四肢伸得板直,手指也抽在一块,浑身不停地抖动,牙齿也咬的嘎哒嘎哒的直响。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真不知该怎么办了。只喊我妹妹:“润秀,快去叫虎仁婶婶”,(虎仁就是原三义泉公社学区领导李志勇)因她们家离我们家最近。我将母亲扶的坐起来,以前听母亲说过,我姥爷给人急救时掐人中,我一手扶着母亲的头,另一只手也试着掐母亲的人中。此时根本顾不上管父亲了。不大一会儿,虎仁婶子就来了,不知妹妹和虎仁婶子怎么说的,虎仁婶子将她一个院里住的玉虎伯伯也叫来了。这时我像盼来了救星,有了大人也就有了依赖,虎仁婶子接替我抱住母亲,不停地叫喊:“德娃嫂子,德娃嫂子,你醒醒,你醒醒”!喊了几声,母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睁开了眼睛,看见虎仁婶子:“噢,他婶子,我的润桃哩,”边说边环顾四周,没有发现她的润桃,又“哇”的一声哭出了声:“润桃呀,你怎在外面哭不回家”!虎仁婶子看见母亲的伤口还在流血,就从灶膛里铲出一铲灶灰,抓了一把敷在母亲的额头上,还真管用,血竟然止住了。 玉虎伯伯一进家就上炕扶我父亲,又是喊叫,又是给父亲揉搓四肢,过了一会儿,父亲的四肢也自如了,也能说话了:“玉虎冈,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老天爷怎么这样惩罚我,叫我缺胳膊断腿都行,不要往我心上捅刀子,我这人家怎过呀”!“德仔,你这说的什么话,你撂了一个女儿,不是还有一儿一女吗,照样是青枝绿叶的人家,不要多想,你是个男人,是家里的台柱子,要照顾好孩子和媳妇。”玉虎伯伯用宽心话开导了一阵父母。虎仁婶子把母亲的脸擦洗干净,母亲的情绪也平稳了。这次的危机总算过去了。 经历了这次变故,母亲的精神垮了,在炕上躺了近一个月,很少吃东西,整天以泪洗面。多亏有我和妹妹,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后来母亲说,那时如果没有我和妹妹,她也不想活了,就怕我们成了没妈的孩子受罪。父亲那时是大队主任,工作比较忙,整天很少回家,只是叮嘱我和妹妹,照顾好母亲。那段时间我和妹妹始终围在母亲身边,尽量让母亲高兴,尤其是妹妹,坐在母亲的脸前,拍着小手说童谣:“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说完忽闪着大眼睛问母亲:“妈,几时给我娶媳妇呀。”“傻孩子,你是个女孩,只能嫁女婿,等你长大了妈给你找个好女婿。” 有一天,母亲早早地起床了,给我和妹妹做饭,看得出,母亲是强支撑着起来的,她走路都摇摇晃晃。从此不论母亲做什么,我都帮忙,体力活由我做。从那时起母亲落下了病根,身体虚弱的很,经常失眠头晕,眼一黑就栽跟头,时常卧病在床。为了给母亲治病,喂了一年的猪羊,杀了也舍不得吃丁点,全卖了,仅能供我和妹妹享用的就是杂碎。 对于我们家的遭遇,村里人都投来同情的目光,更有热心人还提醒父母,要不要讲讲迷信,看是住的地方不好,或是有什么说道。不知是巧合,还是真有说道。我在窗台外面不远处盖兔窝,挖了一尺深的根基,竟然挖出了一付人骨架。听母亲说,在我们房后面不远处,六零年生产队挖地窖时就挖出过人骨架。照此来看,我们是住在一处古坟上,按距离估计,在我们住的房子下面应该还有一处人骨架,所能见到的应该是三辈人。再遇上我们家连续夭折孩子,人们不免产生联想,但父亲是个不信邪的人,母亲几次和他唠叨,再另找地方盖房子,他都不理。 又过了一年多,母亲又生了我小弟,由于有以前的失子之痛,父母把这个儿子当成宝贝,时时关爱,处处小心,生怕有什么闪失。母亲拉扯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奶水不足,生下小弟,随着孩子的生长,没几个月奶水就不够吃了。那时村里有北京知识青年,在他们回家时捎带点奶粉,但在喂的时候,也是以小米糊糊为主,少掺和点奶粉。那时我们家基本上是家徒四壁,那能喂起纯奶粉,如果没有以前的失子,父母恐怕是不会给小弟添点奶粉的。 父母的用心没有白费,不知不觉小弟长到三岁,身体虽然不胖,但也健康。我和妹妹也对小弟疼爱有加,一没事就逗小弟玩。小弟很聪明,我的一手势或眼神,他就能知道我让他干什么。有一次我和妹妹逗小弟,小弟拿起个纳鞋底用的针钗子,我看了小弟一眼,又看了妹妹一眼,小弟就毫不犹豫地拿针钗往他姐姐的脸上扎。我也没想到他会真扎他姐姐,拦也来不急了,一针扎在妹妹的脸上穿到嘴里。妹妹疼得边哭边找我父母告状。为此我第一次挨了父亲的打。 这年刚过完正月十五,父亲就去丰镇开三干会,父亲走后不久,天就开始下大雪,那年的雪特别多,一连下了好几天,积雪的厚度足有半米多。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小弟生病了,又是高烧。父亲不在家,我理所当然承担起给小弟找医生的职责,那时我们住在万金圣,离牛槽洼大队所在地有三里路程。三里路程走了一个上午,我的个子本来就不高,一脚下去,雪就埋到了腰间,其费劲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为小弟治病的信念支撑,可能很难走到牛槽洼。大队医务室有个李爷爷,是公社卫生院精简下来的大夫,李爷爷身有残疾,一条腿先天有病,使不上劲,拄个拐棍,不能走远路,代步工具就是一头毛驴。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七条腿。我找到李爷爷,老人家慈眉善目地对我说:“孩子,你看雪这么厚,爷爷骑上毛驴也走不了呀,爷爷给你配点药,先给你弟弟先吃上,如果不见效,你再来找爷爷。”我带着李爷爷给配的药回到家,就按李爷爷的嘱咐,给小弟吃上了,不多时烧就退了。母亲高兴地说,你李爷爷的药就是灵光,吃上就退烧了。可是到夜里小弟又烧起来了,再喂药,烧又退了。就这样烧了喂,喂了退,退了再烧,一连几天不见效。我又去找李爷爷,由于下雪变天气,生病的人特别多,李爷爷跑来跑去也忙不过来,经常是来了打上一针,又被人叫走了。那时村里别说是有人能治病了,就是连个能打针的人也没有。就这样小弟没有接受连续系统的治疗。过了十来天,小弟的病情,除了没有好转,还日渐加重,已经出现了说胡话的情况,饭也很少吃了。母亲急的直抹眼泪,也没办法,只是念叨着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由于雪大汽车不通,父亲被截在丰镇。那时我的心里也害怕极了,只怕小弟有什么闪失。 有一天早晨起床后,小弟的精神状态很好,也不烧了,还问:“我大大怎还不回来”?还说饿了。这下我和母亲不知有多高兴,母亲赶紧给小弟幹了一碗面条,小弟吃的很香甜。十多天笼罩在我和母亲心头的阴云终于驱散了。我为小弟大雪天找大夫,将两只脚冻得又红又肿,总算值得。吃完饭,母亲叫我快去给李爷爷报信,说小弟的病好了。当我去了大队医务室,我父亲也回来了,李爷爷正和父亲介绍小弟的病情。听我说小弟的病好了,他们听后也挺高兴。 当我和父亲回到家,父亲看了看小弟,什么话也没说,就朝外走了,我和母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我和母亲每天都守在小弟身边,对他的变化反应不敏感,而父亲却不一样,他走时小弟活蹦乱跳,当他进家后,第一眼就发现小弟的情况不对劲。他出去找村里的栓云哥,让他去卓资县的脑包洼,找他大老姥爷,人家能给小孩子治病。因路远又有雪,路不好走。栓云哥和他大姥爷晚上六七点才回来。在这之前小弟已经不会说话了,每隔一会儿就“吱、吱”一声一声的叫,眼睛也没有一点神气。栓云哥的大姥爷进家后,一看小弟的情况,连手也不上了。父母一看老人的态度,就知道情况不妙,母亲只顾抹眼泪,父亲说:“岳叔叔,您已经来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与您无关,我们也不会有任何怨言,您就权当死马医吧”。岳爷爷这才勉强拿三棱针,给小弟头上扎了几针,都不出血了。岳爷爷和栓云哥走后,不大一会儿,小弟就停止了呼吸。这已经是父母失去的第五个孩子了,他们的心理可能是麻木了,没有失去小妹时反应激烈。可我却接受不了眼前的现实,那一夜我陪小弟在地上的莜麦秸上睡了一夜,也哭了一夜。心里只恨地府的曹奶奶太无情,将小弟带走了,我恨不得到地府去,找曹奶奶去理论,和她算帐,为什么对我们家这么无情,不断地往我们的心上捅刀子,尤其是我父母,让他们多时已来,生活在无尽的痛苦中。 第二天,又是三娃伯伯将小弟送出村外,不知扔在了什么地方。母亲没再追,只是不停地念叨:“润兰撂了,润成撂了,忠和撂了,润桃、喜和都撂了……郭德仔!你个脏良心的货,扔了我的孩子你不得好死”!我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母亲将失子的原因怪到父亲的身上,而且还骂得这么狠。后来听我姑姑说,父亲在十几岁时候,去西沟子舅舅家小住,和几个年岁相仿的表兄弟,在海流太四月八的奶奶庙会上玩,将捞儿池里的石头子,捞出几块顺手就扔了。原来母亲是将子女的夭折和父亲儿时的无聊联系在一起了。 母亲的反应虽然没有上次激烈,但她的心仍在滴血,一连好几天冒着外面的风雪,在山头上转悠,找她的喜和。我和父亲都不放心母亲,由我跟着她。那真是受罪了,大风一刮呼呼的嘶鸣,卷起的白毛糊糊,连眼也睁不开,母亲全然不顾。有一天,在村西北的狼窝沟。听老人们说,很早以前这里住过狼,故叫狼窝沟。沟南北走向,不是很宽,但两边的石崖犬牙交错、怪石嶙峋,犹似青面獠牙的鬼怪,特别瘆人,再加上大风一刮,在山沟里听来好似鬼哭狼嚎,给人一种既压抑又揪心的恐惧。我的头皮一阵阵的发麻。但有母亲在我的胆子也大了,跟在母亲的身后,继续朝沟里的一群乌鸦走去,当走近乌鸦群,看见地上一片莜麦秸,再往近走看见小弟就扔在此处,身上的衣服还在,但两边脸被乌鸦啄得基本上没肉了。母亲抱起僵硬的小弟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并且还解开上衣,露出她那干瘪的乳头给小弟喂奶,边喂边说:“喜和快吃哇,你饿坏了哇,妈来迟了,妈来迟了”!乌鸦群在天空盘旋,并不停地鸣叫,似乎是对我们的到来,搅了它们的美餐发泄不满,在这深山里听来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回到家后,我将找到小弟的经过说给父亲听。第二天母亲仍然又去狼窝沟,但小弟不在了,只剩下他穿的两只鞋。母亲看后不仅没有悲伤,反而有一种欣慰的感觉。原来乡间有一种说法,扔出去的死孩子,怕怕(即野生的食肉类动物)遭塌的越快,下一个轮回投胎的越早。后来得知是父亲又找三娃伯伯,将小弟换了一个地方,母亲从此不再上山了。 人们常说苍天有眼,但对我父母这样纯朴善良的农民,却是如此的不公,一次次在他们滴血的心灵伤口上撒盐,在近二十年的时间,接连不断地遭受失子的沉痛打击。 父母虽然一次次地遭受痛击,但他们仍然顽强地同命运抗争,如生长在破岩中的松竹,任凭风雨的侵蚀与冲刷,也不改自己的品格。 经历了失去五个子女的伤痛后,父母这次打定主意,离开万金圣这个令他们永生难忘的伤心地。我们举家迁到了牛槽洼。人虽然住到了牛槽洼,但父母心灵的伤痛岂是一朝一夕能抚平的,尤其是母亲,每当看到与小弟大小相仿的孩子,总不免泪眼婆娑,勾起她无尽伤痛与对往事的回忆。 又过了一年多,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弟,这个小弟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健康地成长,给家庭带来了欢声笑语,也缓解了父母的心痛。随着岁月的更迭,父母的心灵伤痛也逐渐减轻,直到我们兄妹三人都结婚生子,儿孙绕膝,父母总算是彻底拂去了心理阴影。 好人终有好报,如今我和妹妹都有了孙子外孙子,父母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苍天终于还我父母一个迟来的公道,让我父母享受着儿孙绕膝承欢的快乐,也享受着党的政策带给他们的晚年幸福与安康。 作者:郭润和,三义泉镇牛槽洼村人,三义泉中学毕业,年入伍参军,退伍后供职于丰镇电厂输煤车间,现退休。 丰镇同乡会我们都是丰镇人 |
时间:2020/9/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旗县动态丰镇市委编办多种举措强化信息
- 下一篇文章: 7月1日铁路调图,临河火车站最新列车时刻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