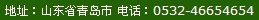|
过去人们物质生活贫乏,日子过得贫困,可年味好像比现在浓,氛围比现在热烈。 过了元旦,丰镇县城十字街的新华书店就把年的味道烘托的浓浓的,一进书店就知道大年来了。那个几乎与人一样高的大火炉生得旺旺的,炉面烧的红红的,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从屋顶到地下,一行行一排排,五颜六色,花红柳绿,全是纸质年画,年画都编了号,你相中了哪张去和售货员一说,售货员立马就给你从柜台里取了出来,一百货、二百货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肉铺前人们拿着肉票,排着长队,等着买肉,谁如果买的肉全是肥肉,没有一丝瘦肉,有人便会羡慕的说:“看!一等肉,多好,全是膘。”副食品公司门口,人们拿着小票,同样排着长队,在买供应的烟、酒、糖、杂棒。大街上的高音喇叭里,不时地播放着王洁实、谢丽斯的歌曲“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家幸福,人人快乐。”家家幸福不幸福不知道,反正我们小孩是快乐的。 大人们在忙着压粉、摊花、炸麻燕、蒸馍馍、花糕、拆洗被褥、打扫屋子、给我们做鞋等一系列过年需要做的事情,总是说:‘耍个哇耍个哇,快别写作业了。” 街外,冰天雪地,年味正浓。天空中不时传来沉闷的爆竹声,火药香与家家煮肉的肉香飘满了大街小巷,闻着就让人高兴,我们全胡同的小孩涌向了大街。扣子掉了,衣服破了,大人们不管,我们也不怕,心想:“过几天就有新衣服穿了,怕啥?”有一年腊月,我与永平,米小,二旮蛋,大眼,三懒机,上灯广场玩,从委托公司的后墙爬上了房顶,走至房檐前,抱住一根电线杆,顺势滑到了地下,那么一个简单而危险的游戏,让我兴奋不已,我还在屋顶捡到了一个小偷扔掉的钱包,里面有王晓棠,杨丽坤的影照,永平和人打架,输了,为了安慰他,我拿出来给他看,令他惊羡不已。 腊月二十六,家里打扫了屋子,粉刷了墙壁,糊了新窗花,贴上了新年画,焕然一新。晚上,姐姐换上了一百瓦的大灯泡,顿时屋内明堂瓦亮,晃得人眼都睁不开。现在只要灯泡太亮,我就有一种过年那甜甜的暖暖的感觉,恍惚间又回到了儿时。 有一回,我与大哥二哥去火车站接父亲,父亲穿着黄大衣,提着大包小包走出站口,我远远地跟在了后面,由于东西多,父亲崴了脚,蹲在地上不能动,我赶快把他们找来,回来后,父亲吃了好多跌打丸,我得到许多黑色的红色的丸药盒子,很是好玩,后来父亲腿好不吃了,我很不高兴,应为我本来答应小伙伴一个人送他们俩个盒子,我的计划由于父亲的腿好而破灭,令我很没面子。 二十九晚上,我让母亲从柜中取出新衣服,看着我的新衣服甜甜的入睡。大年三十,大哥给我们兄弟三人分杂棒,分炮,很小的那种,红红的,绿绿的小鞭炮,这种炮现在已绝迹,现在的人野心大,什么都讲究大。 过年了,母亲与全梅在井台上刨冰,院内亮着灯。瑞平说:“明天点旺火。”我说:“瞎说,全是今天点。”那时我不懂过了十二点便是第二天了,旺火点着了,火苗呼呼冲向夜空,大麻炮震耳欲聋,花炮五彩缤纷,有种五分钱一个的转转炮,左转右转也很好看,仿佛使人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点完了旺火,母亲在红木桌上,摆上了瓜子、果干、麻燕等等……我们弟兄们吃瓜子,母亲每个人给我们泡上一杯黑糖果干水,一家人拉家常,大人们睡熟后,二哥把核桃剥开,放在炉盘上,用秤砣一捣,油浸了出来,让我与三哥看,我现在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有一回我问他,他笑着说:”忘了,还有这事?“夜深了,我们兴奋的不睡觉,我与伙伴们每人手里拿一个纸灯笼,里面点一根小红蜡烛,去捡炮仗,等天快亮时,我们每人捡了满满两口袋。84年,在温成家看春晚,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舞台上的灯光一闪一闪的,坐在炕上的爱兰说,要是彩电哇布景多好看。我心想:“电视还会有色彩?这个爱兰尽瞎说。” 有一年腊月二十三,母亲炸麻燕,我与大哥去东河湾刨冰,临走时我发无聊,把一只白色的母鸡倒扣在竹篓内,回来后母鸡生了一颗蛋,我想:“要吃鸡蛋也容易,只需把鸡倒扣在竹篓内,鸡便会生蛋。”第二天如法炮制,结果令人很失望,晚上睡不着觉,儿时过大年的一些点点滴滴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距现在大约40多年了,恍如一帘幽梦。 百家讲坛的一位老师说:“我们这个星球,从亘古到未来,也许是一只蝴蝶趴在花丛中做的一个梦罢了,我想:”这也许是真的。 作者简介:陈永利,就职于丰镇市林业局,高级技师。对历史有着特殊的感情。游历南北,却对故乡满心热爱。闲来无事,将对儿时生活的感怀和对生活的感激用文字记录下来,与友人交流分享。 赞赏 长按白癜风怎样治疗好治白癜风有什么偏方
|
时间:2017/8/8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丰镇老房子,这里有每个丰镇人的记忆
- 下一篇文章: 丰镇月饼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请成功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