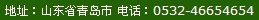|
白癜风的食疗 https://m-mip.39.net/disease/mipso_5967825.html 回忆就像是风筝,虽然线的这头还在手中,但线的那头却早已远去,可毕竟是牵着,那些曾经的往事,怎能忘记。 ——引子刚刚过了谷雨,正是天长夜短,青黄不接的时候,夜儿黑夜就没吃好饭,夜儿黑张的饭是小米稀粥里放了几根面条,母亲把葱切碎,倒点素油,放点咸盐面,拌起来,给每个人碗里放一点,这个可能算作是调味品,每个人吸溜吸溜地喝了那么一大碗。早起起来就饿了,嚷嚷着和母亲要吃的,母亲从容地从门档上取下来一个毛蓝蓝和一个兔儿,毛蓝蓝和兔儿是大年蒸馍馍时蒸下的,这毛蓝蓝是做的花生生的,像一个工艺品,中间有用红枣做的箍子,四周用剪子铰得毛绒绒的,点着红点点绿点点,还有底座,放在那儿很是好看,兔儿还有用红莲豆做的那两个眼睛依然是红红的,放了将近半年多天气了,依然是栩栩如生。按风俗,毛蓝蓝是给女子吃的,兔儿是给小子吃的,但是我最小,有好吃的最后都是归我吃的。母亲从容地取出了那块油黑油黑的擦家布子,“啪啪”的两下,弹去上面的灰尘,那个兔儿爬在柜子上还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我,“咔咔”的两下,在柜子上一拍,毛蓝蓝和兔儿碎成一堆,母亲用手捧着,放入了我的倒衩里,“给你,吃个哇。”有了早点,我兴高采烈的上学去了,一边走还一边高兴地唱着“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发新芽,毛泽东思想普育了我们,快快长大,快快长大!”早上跑操,一跑这毛蓝蓝和兔儿还要往出跳一块,可能是不甘心呆在倒衩子里,我一边跑还得一边不停地用手捂住,它们就在倒衩子里哗哗作响。第三节课是体育课,体育老师扶着两条腿,头从下,双手扶着单杠好像是转这么一圈,我太紧张了,害怕掉下去,就忘记了倒衩里的毛蓝蓝和兔儿了,只听“哗啦”一声,毛蓝蓝和兔儿全掉在了地下,同学们的目光一齐集中在了地下,体育老师慢慢地蹲了下去,“啥东西了这是?”分析着我掉到地下的毛蓝蓝和兔儿,我的脸腾的一下红了,觉得真没面子。过去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要说是没有好吃的东西,也不尽然。主席不是说过么,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这句话还真的是。我小的时候,薛刚山上的杏,大王庙水泊里的鱼,二中树上的榆钱儿,东园水渠边的酸榴榴,这个酸榴榴,有时候我们也叫它酸旺旺,东河湾坝上的麻麻,东山粟子地里的唛,东山上社员拢的葱,东园大队果园的果子,夏天大井里抽出的井拔凉水,秋天在山上烧山药,烧蚂蚱,烧金鸡子(青蛙),校门口的酸榴,一分钱一块麻糖……好吃的东西多的是一时也数不完的。四月初哇也就是,薛刚山上的杏花刚落,杏儿还没有半个指甲大,杏核核都是白的,剥开杏儿还能看见核核里面清凌凌的水了,我们就上山开始摘杏儿了,一个下午,也能摘那么多半倒衩子,再大了,就被别人摘光了,要知道不光是我们老爷庙街的孩子去摘,东园子的,土塘的,毛店巷的,文庙街的,三井窟六井窟的……那的孩子也都去摘了,不几天,还没有等杏儿长大,就摘光了,为了摘杏儿,我还逃过课了,等不得礼拜六下午放假休息,礼拜五下午我就相跟上永平,李志忠,任永红,几个人上山了,凉风习习,神清气爽,不一会儿每个人就摘了半倒衩子,杏树下是我们小孩子欢快的叫声,摘着摘着忽然想到这是逃课了呀,被老师发现咋办啊?看到树下的李志忠时,我们不怕了,李志忠是好学生,是大班长,有好学生领着逃课也不会挨骂的,老师难道不给好学生留面子吗?仲春,二中树上的榆钱儿一哆啰儿一哆啰儿繁繁攘攘的,绿莹莹嫩灵灵,看着就让人眼馋,胆子大的急溜的,三下两下就爬上了树,骑在了树杈上,先是把满把满把嫩灵灵的榆钱儿往嘴里填,看的树下的人是眼馋心热着急火燎的。“快点,快点。”“等一下,等一下,着急啥了,可多了,给你们。话音刚落,一枝满是榆钱儿的树枝扔了下来,树下的人是争先恐后的抢着吃,用手一刷,赶忙就嘴里填,甜个莹莹,水个淋淋,真是好吃这榆钱儿,“再来一枝子,再来一枝子”,树下的人大叫,“给,给,多的就是,一枝枝榆钱儿被不断的扔了下来,树上的人得意忘形,只听“刺啦””一声,树上的人的裤子从裤档扯到了裤脚,“这,这,这”这一会儿也不管了,吃饱后,每个人的倒衩里还要装满满一倒衩子榆钱儿,就走就耍就吃,你推我一把,我推你一下,兴高采烈,等回家了榆钱儿也吃了了。看明人刘佟所著《帝京景物略》里,北京人也有吃榆钱儿的习惯,“四月榆钱初,面和糖蒸食之”不过帝都人吃的风雅些,人家还要把面和榆钱儿糖和起来,还要蒸,我们吃得粗糙些,直接撸下来就往嘴里填。可见这榆钱儿是好东西,北京人都吃。二中还有些个沙枣树,沙枣树开碎碎的黄花,结的果子不好吃,涩的舌头还苦了,不过嘴里有东西嚼也算是聊胜于无,到冬天,偶然树上还会留有一颗沙枣,红红的,抬起头看就向蓝天中嵌着一颗红红的宝石,发现了,我们就会用石头打下来,沙枣落在谁的脚下就归谁吃,别人也不挣不抢,好像这是个约定的规则一样。前几年我见上北山的路上也有一颗沙枣树,不知道现在在不了。东园子大井边的水渠下,常常长着一种叫做酸旺旺的东西,有时我们也叫酸榴榴,红根绿叶上面有些个黑点点,连根带叶都能吃,酸凌凌的酸中还略带甜,我,米小,大眼,二个旦,三民,三懒机,永平,小眼,三后生,我们去薛刚山下的沤麻池耍水时,每人揪上满满的一倒衩子,就走就说就吃,也是蛮高兴的。上薛刚山的路上,碰到了东园大队抽水浇地,水哗哗地流进了水渠里,我们趴在一个真粗真粗的水管口“咯咕,咯咕”每人轮流着喝,井拔凉的大井水水每个人灌上他满满一肚子。兴高采烈的拍着鼓鼓的肚子上山了,就像是北京的阔人在东来顺吃过了涮羊肉惬意地出了前门大街一样。过去的东河湾常发洪水,我们叫发山水了,走到臭皮巷口就能听到轰轰的山水声,站在河岸,就会看到番瓜,葫芦,大木头,有时候还能看见一个个小柜子晃晃悠悠的顺着涛涛的洪水顺流而下,很是壮观。山水过后的沙滩里会有一些个小小的水坑,清凌凌的,里面有一些个小小的麦芒鱼在里面游来游去。我不知道是听永平呀还是大眼告诉我说,这个麦芒鱼可连水带鱼喝下去,下火,解渴还解饿,有一回山水过后,我心血来潮,用手一捧,小鱼儿还在我手里欢快地游着,小小的生灵哪里能知道等待它的是一个什么命运,“咯咕”一口,连水带鱼喝了下去,一股滞泥气鱼腥气,一上午连喝了那么四五条,喝的是一上午的肚子不舒服,估计这鱼儿进了肚子里先是一惊,“哎呀,这是个啥地方了,黑不隆冬的,将将还明堂瓦亮的么,这是咋了。”一会儿在胃酸的作用下,肯定是不舒服了,现在想想,挺残忍的。刚开春不几天,东河湾,新大桥边的土卜塄上就有了丝丝春意,绿绿的麻麻叶子从土壤里钻了出来,我们一伙小孩子相跟上,每人手里拿一个刻铅笔的小刀,来到东河湾,用小刀你划一片,我划一片,各自在各自的领地刨了起来,不大一会儿,一个人手里就有一个留麻麻,这麻麻咬在嘴里辣辣的,一咬还咯层咯层的,这咯层咯层的那是吃在嘴里的沙子,一下午的功夫,也能刨那么多半倒衩子,永平捏从小就细乎,把麻麻一根一根整的齐唰唰的,我哇就那么乱麻团一大堆,吃的时候揪一根。对回刨出来的麻麻上就会有一个小瘩,我们就会一都说,这是个尿麻麻,有人在这尿过,不能吃,其实现在想想也不是,估计是作物的变异。到了秋天,东山上的粟子地里有种叫作“酶”呀也不知道是叫作“唛”的东西,我估计可能是叫作唛,这个叫作唛的东西可能也是作物的一种变异,没有穗子,剥开来里面是一种白白的东西,略带些黑,可能是甜甜的,味道是忘记了,也是年长了,快五十多年没吃过这个东西了。老了就不好吃了,都变成了黑面面了,那也是可以吃的,吃了之后染的嘴唇都变黑了,这打唛也是个技术活,我大哥就很会打唛,进了粟子地,不一会儿,就是一大把,当然一大把唛最后我都吃了。大哥会打唛,二哥则很会摘杏,薛刚山上,看着树上绿油油的全是树叶子,二哥蹲在树下,不一会儿,只听“咯嘣”一声,一个杏就摘了下来了,当然,杏我也归我吃了。大哥会打唛,二哥会摘杏,三哥则很会做火炉子,一到了冬天,就给我做个火炉子玩,我每天提溜个火炉子可二中的操场上跑,一跑火炉子里火还呼呼的叫,我也跟着高兴的呼呼的叫,记忆是很深刻的。我们家养了几个兔子,我们弟兄三人一到礼拜天就上东山拔兔儿草,饿了就偷吃东园子社员拢的葱,这葱在地里长的是齐刷刷的,根子白叶子绿,就像是一个个士兵排成了行,很是好看的。剥开葱后,就会有白白的稠稠的液体渗出,我无端固执的认为那就是牛奶,吃的是又烧心又辣,辣的我还哭了,边吃边哭,边哭边吃,饿死不吃葱看来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薛刚山,东山上还有一种叫做乔瓜瓜的东西,乔瓜瓜可真是非常好吃的东西,甜甜的,好像里面有白白的牛奶了,叶子细细的,开一些个碎碎的小黄花,花了落了,可能是一朵小黄花就会结一个乔瓜瓜,反正是一苗宛子就会结好多,这乔瓜瓜的宛子很不好找,二哥就很会找,看上去是遍地的野草,二哥在地上圪蹴一会儿,剥开草丛,就会发现一个乔瓜瓜宛子,上面结着好几个绿绿的乔瓜瓜,甜个莹莹,脆个生生,真是好吃,如果结的乔瓜瓜很小,还没有长大,我们就会用草埋住,怕别人发现,然后做个记号,等过几天长大再来摘。记得现在的薛刚山的那个洞口就有好几苗乔瓜瓜的宛子了,那时候薛刚山是纯天然的,山上没有这么多的石头台阶,也没有凉亭,山下只有几个沤麻池和绿绿的草滩。薛刚山向阳处的山坳里还有一种小扑棱树,秋天,上面结满了像枸杞一样大的小黑果果,也甜甜的,很好吃,吃的舌头都是紫的。这薛刚山的东南角下还有一个果园,果子刚结下,不大大绿绿的,我们就相跟上一伙孩子去偷果子,悄悄地溜进了果园,刚摘了几个揣在了背心里,只听看园的“呔”的一声,吓得我们拔腿就跑,果子顺着背心溜到了裤腿,谁也顾不上谁,没命的乱跑,吓的心跳的咚咚的,现在想想也是很有趣的。我还在东山偷过社员种的毛豆,我贼眉溜眼的四处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只有空旷的田野蓝蓝的天,四周围是绿莹莹的庄稼,我圪蹴在了毛豆地里,不敢一颗一颗的揪,那样太费事,连叶子带根子拔了三四苗赶快藏在了裤子里,用裤带紧住,赶快就跑,要不说贼人胆底虚,从外面倒是看不出贼赃了,扎的我下身疼的,就那也忍住疼跑下了山,不敢往家里拿,生豆气的也不好吃,后来扔在了新大桥下顺水漂走了。秋天,家家户户会买好多的山药,记得那时候买山药不叫买山药,叫下山药了,为啥把买山药叫做下山药,这个就闹不机迷了。到了礼拜天,我们每个小孩子的倒衩里装上两三个山药,上薛刚山烧的吃,通常是三懒机给看火的,我,米小,大眼,二个旦去捡柴,这烧山药也是个技术活,取的早了,山药结刚发生的了,不好吃,取的迟了,就烧沤糊了,外面是一层黑炭,里面是一点红心心,干脆就不能吃了,一坑山药就报废了,好像是烧糊的时候可稀少了,大部分时候是取出山药来,烧的是虎皮虎皮的,一剥一个沙壳。那年陪读小孩子念书,外一中附近住了两年,孩子上学,下午我没事干,独自一人上了一趟薛刚山,空旷的山峦中,只有呼呼的北风,满目的凄草,我好像看到了三懒机正在烧山药的火堆边说:“永利,快点,没柴了。”我抱着一堆柴,就跑就说:“来了来了。”人去楼空的感觉油然而生,失去了的童年再也无法找回。记得二哥和平安,向东去九龙湾砍酸榴时摘回来几个叫作油瓶瓶的东西,红红的,油亮油亮的,但是不好吃,吃在了嘴里苦涩涩的,还扎舌头了,现在估计那个叫作油瓶瓶的东西压根就不是个吃的东西。夏天,大王庙的河滩里泉眼边,有一种草下长着一种叫作泯水豆的东西,这泯水豆长得圆圆的,灰朴色色的,拔起草来就在草根上长着,现在想想,可能是一种根瘤植物类的东西,在水里洗洗就填在了嘴里,习寡没味,说不上好泯,也说不上个不好泯,不过嘴里有东西,聊胜于无哇。礼拜天不上学,我们还在东河湾靠南的土卜塄上烧过家巴雀,用几块砖围起来,里面放上柴,把雀架在了树枝上,火一着,树枝就烧断了,雀也掉在了火堆里,烧得黑糊糊的,三民给了我一块,我也没吃,看着就不香。好像是他们都吃了记得。那次发小大聚会,他们说还烧过金鸡子(青蛙)吃,这个我一点也没印象,估计他们烧时没叫我的。我倒是还记得在北山烧过蚂蚱,不过我也没吃。我还记得在大王庙的河滩下烧的吃过鱼,冬天的河滩里冻住了许多半寸来长的小鱼,我们一伙孩子刨开冰,兴高采烈的大叫“这儿有一条了,这有一条了”取出了鱼后,架起火,鱼烧着吃,这个烤鱼的味道是非常棒的我记得。记得不知道是谁顾的凿开冰捞鱼,水进了鞋里,取出了鞋垫放在火上烤,最后把鞋垫子给烧了个大窟窿。冬天的校门口大街上还卖一种叫作冻酸榴的东西,也就是夏天的酸榴冻了,落在了地上,勤筋人去酸榴地里用扫帚扫起来,装在篓子里,拿下丰镇,一篓子冻酸榴卖好估计也能卖个四五毛钱大概,卖冻酸榴的穿个烂黑棉袄,戴个棉帽子,棉帽子上的两个扑衫衫一走还一扇一扇的上下动了,就像戏台上官员的帽子一样,车子后夹个烂篓子,里面放一个酒盅子或一个小勺子,一沓子拆好的书本纸,好像是二分钱那么一酒盅子,站在校门口或大街上,也不喊叫,你只要过去,给二分钱,他就会拿起纸围成一个圆锥形,给你挖上一酒盅子或一勺子,冻酸榴酸酸甜甜真是好吃,不论是在学校买上回到班里的座位上吃,还是买回家里吃,都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是讲究的,还要往酸榴里拌一些白砂糖,不过那是有钱人干的。那样就更好吃了。这冻酸榴放在现在依然是开胃,绿色环保的健康的食品。记得一个艳阳高照的冬天,东河湾宽阔的冰面上,我,大眼,二个旦,三民,永平,米小,三懒机,一人一个大马滑冰车,滑的是兴高采烈,热火朝天,三民说,好饿,一下子大家伙都觉得饿了,一人拿尖尖的冰锥在亮亮的冰面上“咔嚓”一声钻一个眼,爬在了冰上,“咕咚,咕咚”,冰凉的河水灌进了我们的肚子里,这凉凉的冰水和肚子好像只是隔了层薄薄的纸,从嘴唇到肚皮都是冰凉的,我就喝就抬头望了望远处灰蒙蒙的薛刚山和黑洞洞的旧大桥。一天下午上体育课,班长杨爱忠远远的从我摆手,就摆手就说“永利过来,永利过来”,我悄悄地地过去,他从倒衩里掏出来一个介菜圪瘩,用小刀切开,我和他一人一半坐在靠二中后墙边的那个水渠边吃了起来,已经是深秋时节了,水渠边的灰菜水备草长的老高,靠东南角有个猪圈,师范学院在里面喂了两头大肥猪,那时我们学校不叫武昌街小学,叫师范附小,这咸菜是太咸了,咸得我们俩是就吃就不停地“吸溜”嘴,这两头大肥猪不知道是闻到了咸菜香还是和我们互动,听到了我们的吸溜声也是一个劲的直“哼哼”。后来做为感谢杨爱忠那半个介菜圪瘩,我好像是带去了一个没有把子的一个很大很大梨,切开后一人半个也在操场上吃了。我的好友蒋存锁的大姐在天津了,所以蒋存锁常常有一些个我所没有的东西,一天下午上学后,蒋存锁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有一个红薯了,下校后咱们上北山烧着吃。”“真的”,我两眼放光,“真的,不信你看”,说着,他拿出了那个两头尖尖,中间圆圆橄榄型的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红薯,多年后,那个人社部叫什么海南的专家说要建设橄榄型的社会,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当年蒋存锁的那个红薯。“赶快装好,看让人看见的”。我推了推他,“嗯,知道。知道”,他点了点头。一想到放学后能吃上烧红薯,我兴奋的一下午的课也听不进去了,就盼着快点下课放学上北山烧红薯,督宁掉胯的就裂过头看打钟的老杨出来打钟放学呀不,白老师骂我了”。“这是咋啦,陈永利,你也是跳的花生生的扎不住了,嗯?紧点回家呀?’’我吓得赶紧坐那一动也不敢动了。放学后,我俩兴冲冲地跑向北山,穿过尚宝才他们那个后院,上好多高高的石头台阶,穿过一个古古的圆门洞好像是就上了北山,迎面碰上了宝才,“干啥个呀,俩家伙鬼迷溜眼的”,“上山烧红薯,你走不?”“走了哇。”不一会儿,红薯烧熟了,宝才笑的牙白灵灵,“看这红薯,一剥一个沙壳”。我现在还能记起夕阳下宝才那个灿烂的笑容。现在的宝才不得了,当了公司的老总,成了丰镇的名人。一次同学的孩子结婚,我和宝才挨着坐,我问宝才,“记得我不啦,”,“哎呀,记得了哇,永利,哪能不记得你了,”“记得咱们和蒋存锁上北山烧红薯不?“记得了哇,那能忘了蒋存锁捏这会儿在满洲里也是买卖做大了,不得了了”,“就数我不行了和你们比”“哎,你也挺好的,永利,孩子也大了,念书了”,“奥,大了,得大学毕业啦”,“看看哇,多快了,一展眼的功夫”,我和宝才说的是兴高采烈,宝才丝毫没有名人大腕的架子。记得我们班有个叫李风英的女生,瘦瘦的,常穿一个红条绒上衣,一天下午上课吃糖,被老师发现,对老师说,我一到下午就饿了,我妈在蛋厂上班的了,给我拿回了几块糖,说几时饿的时候就吃块糖,老师也没咋地个批评,就是说,以后不要在课堂上吃东西,饿了可以下课再吃,一个瘦瘦的女生,下课就饿了,可见这中午的饭也不是多么的丰盛的。我的前排有个姓肖的女同学,叫啥名字真的是忘了,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常穿一件花格子上衣,她的哥哥在部队当兵的了,有一天早上上学后,她给了我一块压缩饼干,这压缩饼干是个啥味道,我真的是忘记了,只记得是好几层的纸包裹着。解开了一层又有一层,那天听人说这个同学已经不在了,令我很是唏嘘了一阵子的。记得还有个同学叫连利枝的,她每天拿好多的含碘片,有粉色的,浅蓝色的,白色的,浅绿色的,这含碘片和去痛片大小一个样,甜甜的凉凉的,含在嘴里神清气爽,感觉夏天也不热了,来了后,每人给一颗,不知道为啥,老也是下午拿了,我们全班的同学围着她,“给我一片,给我一片,整个教室吵吵嚷嚷叫成一片。四十年后老同学聚会,我见到连利枝的第一句话就是“利枝,记得给每天下午给我们发含碘片不啦?”“记得了哇,永利,你真好记性了。”我问她:“你那会儿哪来那么多含碘片了?”她说:“那会儿我爸在牛奶站了,那是给牛吃的。”还有个叫刘建利的男同学,可能是干部家庭,这刘建利长的是白白净净,穿的是干干净净,站在那和我们这些个劳苦大众的子弟比,真的是差别很大的,我们大部分同学穿的是补丁衣服,而刘建穿的是一件虾酱色的恰衣,衣服下面还有两个亮亮的铁环子,在那个年代,那真的是了不起的了,可以说是很了不起了。那回和一个小学同学问起刘建利,“记得了哇,穿个虾酱色的恰衣么,下面有两个亮亮的铁环子”我笑了,刘建利的这个虾酱色的恰衣,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来是给班里的大多数同学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论谁,一说刘建利,马上就想到了刘建利的那件虾酱色的恰衣和恰衣下那两个亮亮的铁环子。刘建利常常往班里拿一种小瓶瓶里面有非常甜非常甜的水水的东西,据刘建利说这个是叫做葡萄糖,刘建利打开了这个小瓶瓶给我们喝,东西太为贵了,不可能就像利枝的碘片一样一人一片,只能是好几个人喝那么一瓶瓶,我们仰起头,张大嘴,刘建利打开后给每个人嘴里倒上那么两三滴,甜莹莹的,凉生生的,这叫作葡萄糖的东西真是好喝的很,为了能常常喝到刘建利的葡萄糖,我给刘建利抄作业,打扫卫生,替他值日,每天跟在刘建利的屁股后,像一个哈巴儿狗,那个谄媚相下贱样,现在想想,都觉得脸红可耻,不过这刘建利一点也不势利不拿大,谁来早了,就给谁喝葡萄糖,为了能喝到刘建利的葡萄糖,我常常起个大早就来到了学校。记得第一回在学校过新年,老师给我们一人一块半糖,一茶杯瓜子,那半块糖是组长给捣开来,分点沫沫,好像那时是从前往后数,一排子分成一组,值日,冬天生火炉都是按组分,这分糖也是按组分,好像是我和一个叫张胜利的同学伙伙分的一块糖,组长永平没有给捣好,捣成了一堆碎沫子,我们只好用大拇指头和二拇指头夹起来吃到了嘴里,咯层咯层的估计是连土也吃到嘴里了,张胜利人大手大,肯定捏的糖沫沫比我多,吃的就比我多,我气哼哼的瞪了他一眼,心里埋怨永平:“那么细乎的一个人,却把好旦旦一块糖捣成一堆糖沫沫,当然了,猜中老师出的谜语也有一块糖了,老师把迷语写在了小纸条条上,让我们抽了,我抽出的谜语是“双木不成林”,打一个字,这么难,刚上一年级的我那能猜中了,正好校长大人来了,说这是个互相的“相”字,班主任老师哈哈大笑了一下就过去了,校长大人替我猜中了谜语,老师也没有给我糖,令我很是不高兴了一阵子的,这个校长是个副校长,长的瘦瘦的,个子高高的,常常穿个蓝褂子,好像是姓王,非常的没有架子,常常是笑迷虎虎的。正校长是康进海,这我记得很清楚,我上早自习捣乱,被一个叫崔树芳的女班长告发,正好康进海路过教室,把我从座位上拉了出来,骂了一顿,揪着我的红领巾说“你还是个红小兵了,嗯?带头捣乱,嗯?把你跳的花生生的,嗯?”校长大人的三个“嗯?”吓的我心跳的咚咚的,以为天要塌下来,其实天永远也塌不下来。那时候不知道为啥,老师们骂人就喜欢骂个“把你跳的花生生的”要不就是“你讨吃连个热门子也赶不上。”我就被教我英语的王老师骂过好几回。另外,吹灭蜡烛也有一块糖了,我是第一个,从座位上用一块布蒙住眼睛走到讲台上去吹蜡烛,那能正好走到讲台上,走着走着就走歪了,不仅没吹灭,挣得了糖,还引来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后来的同学则是站在了讲台前蒙住眼,那肯定一下子就吹灭了。不知道是我从小就笨呀还是扑的太猛的原故。这是一九七六年结束一九七七年的开始,是我在学校里过的第一个新年,也是我记忆里最深最快乐的一个新年!到了冬天,学校家里都生了火炉子,就更有好吃的了,如果家里第一天黑张吃的是馒头,第二天人们就会带一个到学校里,到了学校,一开教室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几个同学围坐在炉子跟前,都甚不甚先把这个馒头从书包里掏出来,放在火炉下,烤的是黄葱葱的,烤过了一面,翻过来再烤另一面,一咬也是咯层咯层的很是香甜的,在火炉边吃完了这个馒头才回座位了,好像那时候班里的火炉子是轮流着生了,轮到谁生火炉就第一天下午放学后去炭房领好了柴和炭,第二天就早早的不等其他同学去就把火炉生好了,现在的学校和家里大部分都不生火炉改暖气了,是方便舒服了,可是我觉得好像是冬天的味道不浓了。家里生了火炉子,就更有好吃的了,饿了就往炉坑里放几个不大不小的山药,过了一个多小时,山药就会烧的绵软沙甜,拿出来一剥,烧的是虎皮虎皮的一个沙克。如果是饿急了,等不的山药熟,那也好办,把山药切成薄薄的片,放在火炉盖子上烤着吃,把山药片一往炉盖子上放,山药片还欢快的“嘶嘶”地叫,不一会儿就冒着热气,再一会儿山药片就烤得黄葱葱的,一咬咯层咯层的也是好吃的,小孩子们发无聊,把水果糖放在炉子上,不一会儿,糖化了,往出一拉,就会拉出真长真长的丝,好玩又好吃的真是。如果有馒头花卷也烤上,如果有饺子那烤上就更好了,更奢侈了。我父亲是在兴和一个叫做什么“报营”也不知道是“宝音”的公社工作,那时候我太小了只记住音了,也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一到了秋天,我们家里永远不缺的就是萝卜、山药、大白菜。秋末,一家人正睡的香了,听到了“啪啪啪”的打门声,兴和的大胶车来了,一麻袋一麻袋的黄萝卜山药蛋大白菜源源不断的抱进了屋,不一会儿,地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将将吃了晚饭,不算是很大功夫吧,黄萝卜取出来在麻袋上一擦,就往嘴里填,甜莹莹,水灵灵,脆生生,这黄萝卜真的是好吃。二哥捏从小就讲究,用小刀刮了,刮一下,这萝卜太嫩了,水还溅到我脸上嘴唇上,溅到我嘴唇上我伸出舌头舔一下,甜个莹莹的,我们弟兄几个就像跌入菜窖的小兔子,围着那几麻袋萝卜“咯层咯层”的,一人吃那么四五个大萝卜,再上炕睡觉。年轻就是好啊,现在让我睡前吃一个苹果,肚子里就了麻扎个挠的,一黑夜并睡了。一开始赶胶车的叫个孙九,脸黑红黑红的,敞着个上衣,穿个黄胶鞋,就像是电影《青松岭》里李仁堂扮演的万山大帅一样。后来公社有了拖拉机,换成了司机赫电奎,这赫电奎也是个大个子,脸也是黑红黑红的,可能兴和人的脸大部分都是黑红黑红的,那时我已经长大了。爷爷和父亲兴和住了三年,可能是刚去第一年父亲给爷买了一斤点心,我爷爷是估计心想,我丰镇还有那么多的孙子了,留给那些个孙子们吃哇,别看平时骂我们这狗的这狗的,有了好吃的还是想留给我们吃的,那个年代的点心,那可是高级奢侈品。三年后,爷爷从兴和回到丰镇,和我们说是有好吃的了,解开层层包裹,里面是一个黑狗娃儿帽子,帽子里是几块圆圆的点心,一股恶朴气扑面而来,众人就笑,以为是啥好东西了,谁也不吃爷爷从兴和带回来的好吃的,油灯下,爷爷骂我们,“这狗的,惺的,点心还不吃了。”“哎呀,这老汉,半念捏还抬国的了,我当早吃了,快扔了哇,并结吃了,看吃坏的哇。”“快拿来哇,你们不吃俄吃,可惜了的,造孽了,白面东西供神了。”父亲紧抢慢抢,爷爷且说且就把点心泡在了稀粥里,吃的是咯嘣咯嘣的,过去人的眼里,东西就没有保质期这一说,可奇怪的是吃了过期东西,啥事也没有,也不知道是咋回事。记得我奶奶给外贸的一个侉子哄孩子了,我们家就让那个侉子给买兔子头了,兔儿头是五分钱一斤,一斤能买那么四五个,差不多是一分钱一个,五毛钱就能买那么一大网兜,过去的人挣的少,可那钱可是真的值钱。花五毛钱就可以炖那么一大锅香喷喷的兔儿头,这兔儿头也是我记忆中的美味。大年家家户户要压粉,我在大年压粉时甚不甚先挑上一碗粉,切点葱花,放点生油,咸盐面,再倒上点醋,香喷喷的能吃那么一大碗。要是家里准备吃糕,第一天母亲就会浸莲豆做馅子,当莲豆快熟的时候,母亲就会拿勺子给我挖上半勺子莲豆,我圪蹴在三民姥姥的小房子墙下,一颗一颗地往嘴里填,就吃就还数着数,一颗,两颗,三颗……红莲豆是沙甜沙甜的,真是既好吃又好玩的。大年下包饺子,大人们拌好了饺子馅,要知道饺子馅的甜咸味道如何,就用勺子挖上半勺饺子馅放在火炉上,就让我用筷子扑拉着,不大一会儿,饺子馅就在勺子嗞啦嗞啦的响,屋子里飘满了饺子香的味道,我马上吃一口,这饺子馅炒着吃真是香喷喷的,记忆犹新的。大年榨完了萝卜蛋蛋的水,人们也不舍得倒掉,放在了火炉子上,熬啊熬,熬啊熬,水越来越少,越来越稠,屋子里就闻到了淡淡甜甜的味道,最后能熬那么稠稠的半茶缸子糖芯,这是留着大年吃糕时沾着吃糕的,这个糖芯不要说吃糕了,就是拿筷子挑一点,放在嘴里,也是甜莹莹的蛮好吃的。还有一种好吃的是叫作油渣渣的的东西,炼完了大油,锅里边就剩下了黄葱葱碎渣渣,用锅铲铲到碗里,放点咸盐面,一咬咯层咯层咸浸浸油香油香的,也是蛮好吃的。放了学饿了没吃的,打开笼屉空空如也,就翻开笼屉底子吃个卷,现在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啥是个卷了,就是蒸馒头是火小从笼屉齿子下头流出来的白面条条,据说弟兄们多,还有因为抢吃个卷打架的了,这个卷我也吃过,不好吃,硬的还咯嘴了。大人们坐在院子里歇凉瞎啦呱捣西游,说的乏了,“去,叫孩子们到嚷到厂(酿造厂),换豆腐干吃哇,不知道为什么丰镇人把酿造厂叫成嚷到厂,这真的是搞不机迷了,搞民俗的专家应该是研究研究。有的回家挖小米,有的挖黄豆,我们小孩子端着去嚷到厂换回来豆腐干,就吃就呱啦,这嚷到厂的豆腐干是红儒儒的烟熏味烟熏味的,咸个滋咸个滋的,也是很好吃的。记忆中的好吃的,还有一种叫作四环素的东西,这个叫做四环素的东西其实是一种黄药片片,为啥叫四环素而不叫五环素或者六环素,这个就闹不机迷了,这个叫做四环素的东西和现在的牛黄上清片是一样样的,圆圆的扁扁的,这四环素真是好吃,甜个生生凉个莹莹,不仅吃在嘴里是甜的,就是到了嗓子眼都是甜的。不过这个叫作四环素的东西可能是稀有特别为贵,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会给吃的,除非生特别重的病,才会给吃上那么一片四环素。记得是一个冬天,为了能吃上一片四环素,我在东河湾吃了许多的冰凌,喝了好多的冰水,站迎着呼呼的西北风在河沿上站了一个下午,回到家里,愣是不咳嗽,也不肚子疼,让我很是沮丧,装模作样的咳嗽了几声,结果母亲理也不理,最后也没有吃到那甜莹莹的四环素。秋天,焖一锅萝卜,吃不了的小萝卜就用线串起来,吊在了房檐下,晒成萝卜条,干了以后当零食吃,一咬咯筋咯筋的,甜莹莹的,是很有嚼头的。有时候把咸萝卜也串起来晒成萝卜条也是非常好的零食,那时候班里的同学就常常往班里拿这个咸菜的,下课来当零食吃的。当然啦,最好吃的东西就在“吉中香”,这“吉中香”在老爷庙街人心中的地位,等同于现在“华林商厦”在现在丰镇人心中的地位,“吉中香”小铺除了卖酱油,醋,咸盐,黄酱,太阳烟,麻纸……我们小孩子不感兴趣的东西外,还有好多让我们小孩子流口水的东西,一毛钱就能买九块水果糖或者是螺丝糖,一毛三分钱二两粮票的月饼,一毛五分钱就能买一个虚腾腾的面包,现在的面包真的是不能和过去的面包比的,现在的面包嚼在嘴里就像是嚼了团烂棉花,习寡没味,凡是吃过过去丰镇老糕点厂面包的人都知道过去糕点厂的面包是个啥味道,放在那个黑黑的铁盘子,一排子一排子的,四四方方外焦里黄,光看外面那层颜色,就会让人流口水的,不要说是吃在嘴里面的感觉了,我真的是才疏学浅语言匮乏,写不出我们丰镇过去糕点厂做的面包味道。我们常常买的是五分钱一包的山楂面,五分钱那么一小包,用纸包着酸酸甜甜的,常常吃的是舌头发红,牙根发酸,我记得大眼就可能买的吃山楂面了,我也想买,可我哪有那么多的钱了,五分了呀,大人给上一分钱就赶紧的花了,到哪攒那五分钱了,那达好不容易了。小铺还卖柿子皮,贰分钱就可以买好多,柿子皮是真不好吃,苦涩涩的,略有点甜味了不过。小铺还卖一种叫作伊拉克蜜枣的东西,伊拉克蜜枣不常有,是来了一批就卖,卖完了就拉倒,一说“吉中香”来了伊拉克蜜枣了,人们传十,十传百,争先恐后从家里拿上大盆子小盆子一盆子一盆子的往家买,这伊拉克蜜枣甜的兴脑子兴脑子的,过去的蜜枣和现在的蜜枣不一样,也不知道是咋的了?现在的蜜枣是一颗一颗的,过去的蜜枣是一圪蛋一圪蛋的。“吉中香”小铺还有两样东给我印象最深,一个是一块七毛钱的橘子罐头,一个是一块五毛钱一瓶子的橘汁水。橘子罐头吃过,橘汁水没喝过,橘汁水的瓶瓶比橘子罐头的细,从外面看黄澄澄的橘子水很是诱人,标签上也画了半个掰开的橘子也是黄澄澄的,感觉一定好喝,听说是兑上水喝了,瓶瓶上有些个玻璃花点点,看上去更加诱人了,现在这个橘汁水失传了,没有卖的了,不是哇买上一瓶子喝喝它,到底是个啥味道?如果我生病了,躺在炕上半天不出个耍,母亲就会过来用手摸摸我的头,“呀,这孩子这是咋啦,咋烧些个这了?”然后就给我化一杯红糖水。如果喝了红糖水不管用,就去吉中香买五毛钱的果干,如果是喝了果干水还不管用,母亲就会大破大舍地去吉中香买回一橘子罐头,这橘子罐头是甜莹莹凉生生,吃到肚子里是神清气爽,马上就不发烧了,也不难过了能出个耍个啦,那甜个莹莹的罐头水喝下去能从嘴唇一直甜到肚皮,好像肚皮是一层薄薄的纸,连肚皮也能感觉到这罐头水是甜个莹莹的,真是好了。现在想想,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事情,不用打针,不用输液,一个橘子罐头就治好了病,再也没有比这奇怪的事情了,为啥过去的罐头就能治病,这个我也是真的搞不明白了。有一年去呼市,一个从红砂坝站上车的女人年龄和我相仿,车上没事干拉闲片,说东说西,说古说今,她和我说“你说那会儿就奇了怪了,捏难过的多厉害,去供销社买上个橘子罐头,吃完捏就了头清头清的,达不难过了,病也好了,捏也不知道是咋的了?”我笑着点了点头,想起了孔子说的一句话“与我有心戚戚焉!”丰镇城南旧事(一)丰镇城南旧事(二) 丰镇城南旧事(三)丰镇城南旧事(四) 丰镇城南旧事(五)丰镇城南旧事(六) 丰镇城南旧事(七)丰镇城南旧事(八) 丰镇城南旧事(九) 作者:陈永利,就职于丰镇市林业局,高级技师。对历史有着特殊的感情。游历南北,却对故乡满心热爱。闲来无事,将对儿时生活的感怀和对生活的感激用文字记录下来,与友人交流分享。 丰镇同乡会我们都是丰镇人 |
时间:2020/8/1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丰镇市4月5日在线教育空中课堂播出安
- 下一篇文章: 五一小长假去哪玩,在浙江除了西湖,这些好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