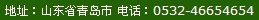|
我离开插队落户的丰镇九龙湾河畔生产队,到今年快五十年了。在插队的岁月里,我参加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砍过垄道,掏过大糞,放过牛,顶工跟过皮车。这些营生,记忆最深的是跟车上窑拉炭。别看就一两回,记得可牢哩,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一 “车轱辘一转,烧酒纸烟不断”,这是当年社员们对车倌的说法。在那个年代,赶皮车是个好营生,有罪沒苦,挣得工分又高。冬天上窑拉炭,住大店、下馆子,车倌是队里头见世面最多的人,也是村里头故事最多的人。 “樱桃好吃树难栽,朋友好为口难开”。车豁子(丰镇地区对赶车的一种称谓)们跨在车辕子上,嘴里头哼着小调调儿,手里头挥动着长鞭鞭儿,“得——驾!”得得嗒嗒,二匹拉套的马双摱蹄子奔跑着,辕马也随配上跑。坐车的男女人紧抱住车塌栏,大车颠达得,屁股也不敢挨车底扳,心里头圪抓抓,嘴上还笑哈哈,好像十分开心的样儿。有的年轻后生还专门起哄,鼓搗上车豁子打上马再跑。“啪啪”又两鞭子,车跑得越发快了。坐车的人们双腿也圪蹴不住了,?蛋子敦得生疼,嘴里头还喊叫着“真虚乎儿!”车渐渐地慢下来了,车豁子腰扳直溜溜,脑袋圪晃晃,“乱席篇”随云流转,悠悠自得,真有点儿忘乎所以的样子。 二 我不喜欢憋屈在大田里干活,成天价跟在一伙女人的屁股后底,听着她们叨啦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和一些不充耳的晕段子。 我虽接受了一年多的贫下中农再教育,仍然有一股子小资调。喜欢眺望远方的大山,喜欢遐想远足天下的美景,喜欢遥想远处会有奥妙可寻…… 放性口也是不错的营生,但时间长了一个人太憋闷,枯燥无味,久而久之有点儿厌倦。我思慕着跟跟皮车,倒是挺有意思:能到矿上拣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能到山沟沟里头砍一些酸梨儿(沙棘)。拉炭回来,让伙伴们围在油灯下,吃着酸梨儿,酸得他们不住地叭啧嘴。再听上我述说着路途中乱七八糟的趣闻和车马大店的故事,挺有意思。 我们生产队有两挂皮车,一挂是拴奎赶车,喜喜跟车;另一挂是永生赶车,二牛跟车。有一次,喜喜病了,一时半会儿不能出车,趁住这个黒拉子,我取得拴奎的同意,生产队长的批准,顶工跟了车。这一下子,实现了我的夙愿,能体验体验打尖住店,睡大炕,吃莜面的味道儿。 跟车的营生比较简单。空车时候,可以面迎天躺在车底扳上,铺上干草,枕上行李,盖上白茬子皮祅,望着蓝天白云,丢盹瞌睡;不时地听一听车豁子们吹牛拍马,捣拉些无影传的故事;还可以大饱耳福,听听车豁子们亳无顾忌的原声态演唱。重车路平的时候,也能坐在后塌栏上歇一歇脚。下坡时,用劲儿拉紧磨杆,防止跑(音pao)坡;上坡时,要审时度势地掖掖车,防止滑坡。装车卸车倒是挺乏得。要知道挣得工分虽没车倌高,但比做别的营生挣得多。还有,你要想当车倌,就得从跟车学起,一步一步地慢慢熬摸。 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城里。父亲一直是个赶车的,对赶车这营生,情有獨钟。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有幸能跟皮车,心里边二个字一一高兴。你看哇,马车一上路,车豁子们大鞭子一甩,拉车的三匹马一跑,铃铛子叮呤咚隆一响,车倌腰带丢溜着的牛角刀,前后摇晃,耀武扬威,得确让人羡慕! 红樱子穂穂的大鞭子是车倌的标志,它的用途不用细说。可牛角刀我得说一下:牛角刀是车倌的另一个标志和象征,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修补绳线、整修牲口笼头。在路上,万一翻了车,为及时解救驾辕的牲口,就得赶紧用这飞毛利刃的牛角刀,三下二下,把套在牲口脖子上的绳线和笼头割开,以防勒死。 三 “哎!二先生(我的外号)下坡了!慌慌儿拽紧磨杆!”在皮车左侧与驾辕的大黑骡子并行的拴奎,脚穿一双牛毛毡勿拉,右手高高举着红缨穗子的鞭子,嘴里喊喝的声音非常洪亮,这分明是有意识地在提醒我。 三匹性口拉着车,皮车上圪压压地装了一车炭,在冰倒擦滑的土路上,圪吱圪吱地前行着。我们的车,拉长套和拉边套的是两匹枣红色的骟马。拉长套的马儿岁数大了,挺听话。驾辕的则是一匹身高力大的大黑骡子。上坡时三匹性口,在拴奎的吆喝下,齐心协力地使劲拉;下坡时有经验驾辕子的大黑骡子,四个蹄子杵地,用?蛋子紧紧顶住后座桥,不让皮车往下出溜得太快。我听旺子说,不少皮车因为坡太立,驾辕的牲口搓不住坡,跟车的又拽不紧磨杆,翻车跌到沟里头,弄下个车毁人亡的亊儿,时有发生。 这次拉炭,我们队里头二挂皮车,三挂牛车,全出动了,浩浩荡荡一长溜。牛车走得慢,逐渐相跟不上了。我们二挂皮车一前一后,一直相跟着,拴奎是头车,永生随后。 拴奎是我们九龙湾壕堑大队有名的“车豁子”,在“嘚儿嘚儿,喔喔,”的口令下,听说的牲口拉着车,时儿左拐,时儿右转。一路小跑。 下坡的时候,两挂皮车拉开了距离,那是怕后车搓不住坡,和前车撞上,发生车祸。 我后侧着身子,双脚紧紧杵着地皮,使劲儿拽着磨杆。皮车发出了“吱吽吱吽”刺耳的噪音,就和高音二胡没定准线一样,在空旷的原野上飘荡着。声音高低不一,交错起伏。听着这声音,牙碜圪搗的,但我心里头感觉还是挺痛快的。 你听!每挂皮车的磨杆发出得音响都不一样,吱吱吽吽就像一曲不协和的长调。嗨,世上最高明的“调音师”,我看也没法子把这刹车的音调,调得悦耳动听些儿。 一路上,我们二挂皮车一前一后。从一打早到太阳落,除了响午打尖,歇息一会儿,走了整整一天。这一天,大约摸也就走了个百十来里地。 寒冬腊月,夜长昼断,人困马乏。在太阳落山时,看到了坡底下有一处车马大店。我满以为住店呀,可拴奎鞭子一甩,继续往前走。葫芦里卖得什么药,也不知道。后面的大车倌永生也不做声,我们俩个跟车的也没资格说话,只好一齐赶路。大概又走了有个四五里地,路边边有一处车马大店,拴奎兴高采烈地吆喝着性口拐进了店里头。 四 这个车马大店叫红四店,有五六亩大的一个院子,十来间大房和几十间坐东朝西的马厩。当院有一口辘辘井,井台边有一不溜饮牲口的石槽子。院子里不远不近,还栽着好些些拴性口的石头桩子。 为了夜里头好照料车,拴奎把车停在了房子窗户前的空地上。我先把拉套的两匹马儿卸了绳线,拴奎把驾辕的大黑骡子卸去鞍子、辊肚等,用“又”字型的木头顶车的架子,把车支了起来。我又搬了二块石头把车轱辘掖住。 我和二牛把牲口拉到马厩。回头又从车上拿上草料倒在槽子里,大黑骡子抬着头,像是感谢似地冲我点晃了晃脑袋,然后低下头大口大口嚼吃起来。 拴奎告诉我,刚卸下套的牲口,得先喂草料,等得吃饱了,落了汗,才能给它们饮水,不然的话牲口就会生灾患病。稍后,我又拿上马灯查看了查看拴马的缰绳,歇心了,这才回到大店的房里头。 我进了大店的家一看,偌大的一片窗户,仅仅有四孔玻璃,其余的全是用麻纸糊的。窗户边挂着好几串干红辣椒子。一口大瓮靠墙根根放着,瓮沿上挂着一把铜盛水子,不用看就知道那是水瓮。其余还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瓮,能闻出来,这些瓮里头放得是,用黄罗卜和有茴子白淹得乱淹菜,这是给住店人支预的。一口出勺大铁锅稳在硕大的锅灶上,盖着分为两半的木锅盖;锅台上还垒摞着好几节出勺大笼净。大锅灶的另一头还连着一个小锅灶,小铁锅里的水滚开着,热气充满了整个房间。一个大风箱同时吹着一大一小锅底下的火。锅台连接着两盘大炕,左手边的那盘大炕要是睡满了人,最少也有个五六十号人。听拴奎说,右手边的那盘小炕一般都是店掌柜和孩子们睡觉的地方。小炕的炕头上放着一卷儿行李。大炕上没有行李,只铺着几圪达高梁炕席子。那时候铺盖都是车倌们自备,多数车倌的铺盖卷儿都装在麻袋里。 拴奎在我拴马、喂草料的时候,已经把我们的铺盖卷儿提?到大炕,温上咧。随车带的莜面也拿到了大店里。店掌柜是个老扳娘,她早就洗了手,把莜面倒在大瓷盆里,张落着和面推窝窝。 老扳娘就说就做营生。“奎哥来了?哎哟,有些时候没见了”。“嗨,前段时间忙乎着交公粮,这才闲下没几天天,就来拉炭了。趁这几天没下雪,队里头让给社员们拉点儿过冬炭。哎,你也挺好的哇?”拴奎回应着。 拴奎、永生和二牛三个人盘腿坐在大炕上,一人一杆烟锅子,用手往烟锅得老里拧烟叶子。拴奎的烟袋杆子不太长,烟嘴子是墨绿色,还是玉石的,挺精致。人们说用玉嘴子抽烟,不烫嘴,也不上火,所以玉嘴子就成了上乘东西了。听说有人拿莜面和胡油换拴奎的这个烟嘴子,他贵贱也舍不得。村里头人都知道,那是拴奎对象送给他的订亲物。他经常不声不响地摸捞着烟嘴子,我怕引起拴奎丧心,一直也不好意思问他。 二牛抽完两袋烟,叫上我,出去给牲口切草。那个时候没有切草机,是用铡草刀切。这营生是有技巧和技术的,两个人必须配合默契,这样才切得又短又快。我是第一回切草,二牛怕我把手切着了,他添草我切。可我怎也掌握不了切草的那股巧劲儿,半天切不下多少。二牛看看不行,我俩人又调换了一下。我看着那寒光闪闪的侧草刀,心朴嗵朴嗵地直是个跳,手抖挞得好赖抱不紧干草……,后来在拴奎的示范、指导下,我总算掌握了切草的要领。 五 夜幕降临了。过路人,长途车,都像迁徙的候鸟儿,一起挤在车马大店里。正当大家呱啦得热色时候,我瞭见从车马店的大门,走进两个人。走在前面的老汉,歩数儿圪圪擦擦地,看上去有把儿年纪了。老人家手里头拿着一根木棍棍,木棍稍稍被后面的人紧紧地拽着,看得出那是个没眼人(盲人)。没眼人的脊背上斜挎着一条长蓝布袋子,老汉背着行李,说是行李,其实就是两圪塔烂羊皮褥子。 俩个人还没走到房跟前,老扳娘就笑嘻嘻地和大家说:“今儿晚上店里头又热闹了。堡子湾的马山老汉和三没眼,讨吃念喜路过咱们这儿,来住店了”。“哎,一阵儿让他们俩个人给咱们好好唱达上几段!最好哇,能给唱一唱《小寡妇上坟》,或是《光棍哭妻》。哈哈哈……”,车豁子们高兴地笑了起来。 马山大爷领着三没眼来到了大店窗户前,没着急进家避寒取暖,按要饭的规矩,站在窗前头,扯开大嗓门高喊着: 走进大店喜气升, 大店里面住贵人。 闲下没事解解闷儿, 听听要饭的唱几声。 这时候,三没眼把后背的蓝布袋子摸捞着解开,取出一把铜壳子四胡,挂在腰带上,左手摁弦,右手拉弓。随着左手四指在琴弦上下的按动,原生态的调调,伴随着变化不大的节奏唱了起来: 冬天的大风实在冷, 冻得人们脸皮子疼。 老汉我拿根木棍棍, 后面拉着个没眼人。 车马大店生意隆, 寒冬腊月暖人心。 大炕上坐满了一家人, 可怜我这讨吃要饭人。 上炕想和大家喝几盅, 喝几盅…… 酒足饭饱, 再给大家瞎哼哼, 瞎哼哼…… “快进来,外面冷哇哇的”。老扳娘热情地迎了出去。看来马山大爷和三没眼是常客,住车马大店的规矩是知道的。进屋后,拿出沿村要来的莜面,老扳娘挖出两大碗,倒在大瓷盆里。 在车马店里头吃饭是按人计量,店里头出辣角子、咸菜和大烩菜。万一有人实在拿不出莜面,也没啥,大伙儿每人少吃一口就够他吃得了。那时候,虽然贫穷落后,但是人和人之间是非常友好的,没有歧视,谁也不黑紫谁。 六 车马大店“打平伙”是常有的事。有句俗话:有酒没菜,不算慢待。 烧酒会有的,那就是把随车带的马料(莜麦、高粱、黑豆等)拿出去换烧酒。那年代出门在外,车豁子们也就图得这一口。换烧酒,这营生也就是我们跟车小后生的亊儿。 炕桌上温热的一壶薯干酒,一大盘烂淹菜,一碗五香大豆。几个磕碰的有了小豁豁的酒盅子,昏暗的油灯,围坐在炕桌周围的车倌们,墙壁上晃动的人影,锅台上慢慢升腾的热气,这一切展现出了车马大店的特有氛围。那毫无约束的叫唤,面红耳赤的划拳猜令,把这种特有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我跨在炕沿边边,一是为了少喝点酒,二是看看老扳娘和莜面、推窝窝的那个利索(音同色)劲儿。我无意识地回过头,看见拴奎一眼眼瞅着老扳娘的身影,那眼里流露出光棍儿渴望已久的目光,就和发情的儿马,瞅着骒马的屁股蛋子一样。老扳娘也知道有人在注视着她。她一点点也不在乎,心里头倒喜欢让车豁子们看她,不由地走路也拿捏起来,做饭也扭腰曲胯,拉风箱也是挺胸抬头,为的是招惹男人们的眼珠子。后来我知道老扳娘是二后生媳妇儿,是个苦命的女人,她男人二后生死了有好几年了。 听车豁子们说,有一年冬天,农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高潮,红四生产队在村南头打大井时,几声炮响,二后生就在硝酸氨炸药的烟雾里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队里头出钱给割了一口棺材,把他安顿到地下休息了。 为了照顾他们一家人,队里让二后生媳妇当了车马大店的老板娘。车马大店的收入归集体所有,二后生媳妇只挣个工分和拿点儿补助。孩子由公公婆婆照料着,她成天吃住在店里头。这是一种难以忍耐得寂寞和孤独,二后生媳妇有心红杏出墙,但在当时突出政治的时代,她怕队里头人们说三道四,只好把红杏埋在心里。好在有打尖和住店的车豁子们,男女人互相说说笑笑,日走星移,一天一天感觉日子过得还挺快,二后生媳妇的内心臊动也被这劳累扑灭了。 七 二后生媳妇知道拴奎一上窑拉炭,说啥也要来这儿住。拴奎也掐算着时间,赶趁着走。约摸着到了黑张儿,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赶着马车兴匆匆地住进了红四车马大店。 二后生媳妇不时地和拴奎的目光对视着。俩个人相互无声的一笑,二后生媳妇就会感觉到脸上热乎乎的,心也呯呯地直跳,这种快慰,她是求之不得。她知道拴奎对她也有那个意思。二后生媳妇在底下,也曾打听过拴奎的情况。她知道拴奎是娶过媳妇的人。也听说拴奎媳妇,在村里头算得上个漂亮女人。过门才一年来天气,因为坐月子难产,大出血而离开了心上的人。 除了拴奎现在用得,旱烟锅子上的玉嘴子之外,绣着鸳鸯戏水的黒条绒,放烟叶子的布袋子,也是媳妇亲手给他缝下的。从媳妇离开人世后,烟布袋子老在拴奎腰带上揙着。这两件东西成了拴奎伤心和回忆媳妇的物品。拴奎天天嘴里叼着烟嘴儿,就像媳妇时时看着他的嘴巴一样,不让他谈情说爱。可日子久了,心里头的欲火越来越旺,按耐不住,使他的目光在二后生媳妇的身上久久停留。 八 一壶烧酒醉不了人,但男人们喝了酒,本事大了,胆儿也壮了,挣着抢着把一路上的见闻,不管是晕的素的都讲给大伙儿听。 旱烟、老酒把每个人的脸巴子烧得红扑扑的,蒸饭的热气弥漫在整个房间,灶忽的火焰随着拉动的风箱一闪一闪,映红了二后生媳妇俊俏的脸庞,拉风箱时伸展弯曲的胳膊显得分外有力,胸前圪顶顶的乳房,流露着她的干练。 车豁子们和马山大爷、三没眼把一大壶烧酒喝了个精光。饭也熟了。二后生媳妇揭开锅盖,拿转拍拍,莜面窝窝特有的香味随气扑鼻而来。二后生媳妇给大家碗里头,挨个儿舀汤汤。轮到拴奎时,她特意给碗里多加了一勺子。拴奎也感谢地笑了笑。这会意的一笑,代替了两个人不言自明的情感。 大伙儿稀里哗啦的吃着,我也透过浓浓的蒸气,观察着每位不期而遇的车倌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车马大店吃饭。大家的吃相各不相同,不受任何约束,完全是返璞归真的感觉。这也是我后来常常在梦里梦见的情景。 吃饭的时间不长,满笼净的莜面窝窝风卷残云地消失了。这是二后生媳妇忙乎了一个多小时,做好的饭。看到每位车豁子们的满意表情,二后生媳妇觉得忙活儿半天,也就值娄了。 收拾碗筷,刷洗大锅,在二后生媳妇的手里就像行云流水一样,熟练而麻利。大炕上的煤油灯依然忽闪着,屋里的?气渐渐地散去了,窗户上的那四块玻璃也冻成了美丽的冰花,好像雪后的原始森林,维妙维肖。 九 靠着行李半躺半坐的马山大爷,看着忽闪忽闪的煤油灯,说了一句串话儿:“胖蛋儿胖上不了炕,焾焾儿细下不了地”。三没眼赶紧就是个说:“水瓮胖,上不了炕,灯焾子细,下不了地”。 酒足饭饱了,人们还想听一听这两个人的“乱席篇”,我接住说:“马山大爷,您们两人再给我们唱上一阵儿哇!让大家开开心,解解闷!”我不知道三没眼姓甚叫啥,出于礼貌也不能直呼三没眼。永生、二牛和其他的一些车豁子们也跟着叫唤着说:“快给来上一段儿哇!” 昼短夜长,欢聚一堂,四胡一响,曲曲飞扬。吃饱喝足的人们在没有电视,甚至于连个半导体收音机都没有的年代,在磨得黑窟拉窍的炕席上,人们围着一盏油灯,等着听马山大爷他们二个人唱小曲儿。 三没眼盘腿坐在大炕当中,眼睛忽眨忽眨地按捺不住痒痒的嗓子,手里头拉着四胡,嘴里干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和四胡配了配音儿。随着过门儿一响,开场的大幕算是拉开了。 哎嗨,哎嗨嗨! 数九寒冬的天, 刮起了西北风, 住店的客人呀, 爱听我瞎哼哼。 十五的月亮啊, 升在那半空中, 难怪那世上遗留下人想人。 话说堡子湾村有位好医生, 他的医术不赖治病能救命。 骑上洋车走村窜户来扎针, 拿手的是医治风湿腰腿疼。 无论走到哪都有个好名声, 就是有个赖毛病, 啥? 爱呀嘛爱女人。 …… 三没眼有扳有眼,略带沙哑的歌声在空旷的大屋里回荡着,车豁子们神情专注地倾听着有趣有味儿、悠扬顿挫的原生态小调儿。人们的喝彩声,鼓掌声接连不断,接下言的诙谐问答也逗得一屋子人失笑得东倒西歪。哎呀,这“油灯晚会”的演出,真有特色,让大家激情四射。我完全被这土里土气,下里巴人的唱腔深深地吸引住了,长时间地沉浸在悠长的民间小调儿中。要不是憋不住尿,我可真舍不得离开这热乎乎的大炕和存满人情味的曲调氛围。 十 我尿完了回来,夜里的寒风吹得我打了个冷圪生。 “人无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 猛然间我想起该给性口添草啦,我还得出去一趟。 快到马厩时,听到拴奎悄悄说话的声音:“不行啊,我来你村里算个啥?那让我们队里头的人笑话。”又听见二后生媳妇儿说:“我去你们哪儿行是行,可上了岁数的公公婆婆咋办哩?我又不能摱下他们不管!我走了,村里头的人会说我没良心……”我停住了脚步,听到了这神秘而又充满着人情味的对话。我也看到了寒冬腊月马厩里,在马灯昏暗的灯光下,紧紧搂抱在一起的“干柴”和“烈火”。我生怕打搅了这俩个人的温存,悄悄地退后了几步,慢慢地转过身,回到了大店房里头。 三没眼还在唱着那风土人情味儿十足的小调儿: 二姑娘借笊篱, 出了门面朝西。 迎面碰见个槍崩鬼, 槍崩鬼不讲礼, 抱住二姑娘就亲嘴, 亲了嘴还不依, 硬把二姑娘拉进高梁地, …… 记得那天晚上,车马店的炕越来越热,烙得我翻过来调过去,暂且睡不着。大概三更天了,车倌们一个个鼾水大作,睡得香甜。我看见拴奎尿完了回来,趁着人们熟睡的时候,在夜幕的掩护下,蹑手蹑脚地上了右边的炕上。那夜,二后生媳妇的盖窝总是鼓得老高老高的,…… 这一晃,我离开下乡的村子,快五十年呀。我老思念着农村插队的日子。当时是艰苦些,但留在我头脑里的故事,记忆真切,人物鲜活。这些亊和人是那样接地气,生活平淡些儿但不乏味,回想起来是十分美好的。 去年夏天。我有幸沿着昔日跟车走过的路,去了一趟大同。一路上没看见一辆胶皮车,路边边的车马大店也无影无踪了。呈现在眼前是一条平坦的柏油路,还有那满山遍野的风电扇和山坡坡上的一大片太阳能硅板。停下车,我极目瞭望,不由得兴趣来了,敞开公鸭嗓子唱了起来: 瞭见那个村村, 也瞭不见个人, 我泪个蛋蛋洒在沙蒿蒿中。 …… 说明:文中所讲述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不必对号。 作者:潘茂增,年10月4日出生,中共党员。年插队落户于丰镇九龙湾公社河畔村。年6月抽调到丰镇乌兰牧骑工作;年底从政,先后供职于丰镇县委、人大常委会、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局,丰镇市新城区、审计局。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赞赏 人赞赏 长按贵阳白癜风专科医院北京哪家医院治白癜风最好
|
当前位置: 丰镇市 >丰镇知青岁月的记忆跟车轶事
时间:2017/10/2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光绪年间的丰镇老家土地房产证,哦买噶的
- 下一篇文章: 丰镇市瑞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携久福中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